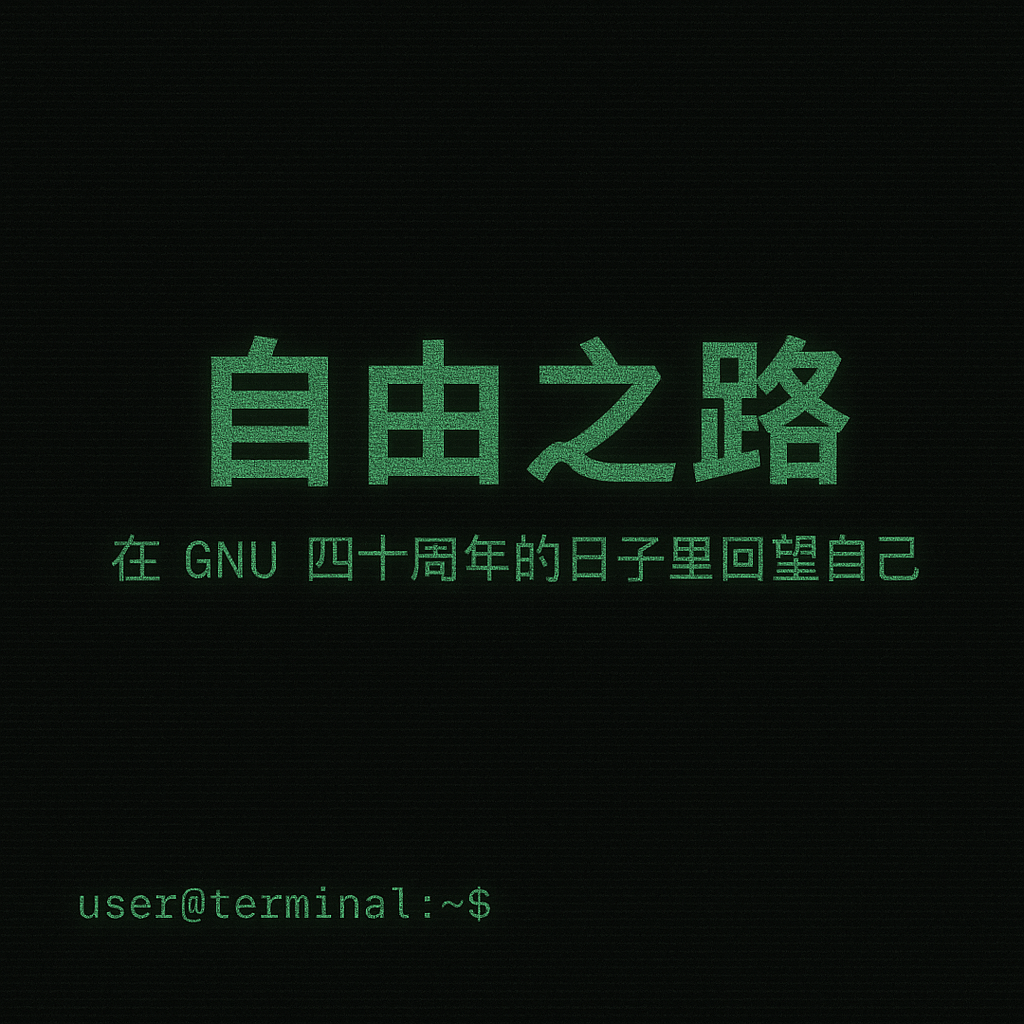
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
对许多技术人来说,GNU 四十周年不仅是一段历史的纪念,更是一种精神的回声。
四十年——人生的大半,一代人的全部。在这漫长的时光里,一个操作系统的未竟梦想,一纸自由软件宣言,一群人在数字世界里默默前行的背影,早已超越了软件本身的意义。GNU 成为了一种对抗技术异化的象征,一种关于”自由”的生活哲学,一面在商业浪潮中依然飘扬的理想主义旗帜。
在断联中重新认识自由
大约一个多月前,我重新读了理查德·斯托曼的传记《若为自由故》。早几年读它,纯粹是技术考古的好奇;这次读,却读出了一些深层的情绪与自省。
那段时间,我正在经历一个主动的”断联期”:休学、关站、清空所有个人内容,刻意让自己回到某种”原点”状态。我不再刷手机,除了查邮件,几乎完全切断了与外部世界的信息联系。
这不是逃避,而是一种主动的内向。就像 RMS 在 MIT 的那些深夜,独自面对终端屏幕的绿色光标——有时候,你需要足够的安静,才能听见内心真正的声音。
在这段封闭而专注的日子里,我写了大约十万字。没有标题,没有读者,也没有发布的计划。只是一个人试着将混乱的思绪写成某种秩序,将模糊的感受雕琢成清晰的认知。那些文字像是我与自己的对话,像是灵魂的自我挖掘。
我开始理解,为什么 RMS 能够在那个个人计算机还是奢侈品的年代,就预见到软件自由的重要性。真正的先知,总是在孤独中看见未来。
开源: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
从 2019 年接触开源起,这些年我在其中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与成长的喜悦。
我遇见了许多奇妙的人:有人热衷在终端里构建自己的数字王国,把每一个配置文件都调教得如诗如画;有人把开源当作传统手艺活来精雕细琢,每一行代码都要反复打磨到满意为止。我们一起维护项目、分享想法、参与黑客松,不为了 KPI 的达成,也没人强迫你提交代码。
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什么叫”出于自由意志的参与”。
在商业化的工作环境中,我们往往被各种指标、期限、汇报所裹挟,很少有机会体验纯粹的创造快感。但在开源社区里,你贡献代码是因为你相信这个项目的价值,你修复 bug 是因为你希望让工具变得更好,你写文档是因为你想帮助后来的人少走弯路。
正如 RMS 在《若为自由故》中所提到的,“自由的价值不只是一个口号,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”
我想,他说的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,而是那种即使没人要求,也愿意承担的责任;即使不被理解,也依然愿意为后人修一条路的坚持。这种坚持,源于内心深处对美好事物的渴望,源于对技术本身的敬畏,源于相信代码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朴素信念。
开源从来不只是一种软件开发模式。它是对抗技术异化的一种方式,是个体在数字时代实现自我价值的微型乌托邦。
在快节奏中保持慢思考
如今我又回到了节奏更紧凑的生活中。课业、项目、各种deadlines重新填满了日程表。但我依然尽力保留写作的习惯📒——哪怕只是每天的几百字,也像是给自己点一盏灯,提醒自己:你依然在那条理想主义的路上。
写作成了我的精神锚点。 在这个信息过载、注意力被无限切割的时代,文字是我对抗碎片化思维的武器,是我与内心深处那个更真实的自己保持联系的方式。
每当我敲击键盘,将模糊的感受转化为精确的词句时,我都能感受到一种类似于编程的快感——那是思维被整理、逻辑被厘清、混沌逐渐有序的美妙过程。
在这个 GNU 四十周年的特殊节点,我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另一层含义:它不只是技术路线的选择,更是存在方式的提醒。
自由,意味着你有选择的余地,甚至有推倒重来的勇气。
结语:慢慢开花的数字花园
四十年前,当 RMS 在那台 PDP-10 前敲下第一行 GNU 代码时,他可能没有想到,这个项目会成为整个自由软件运动的奠基石,会影响几代程序员的价值观,会在四十年后依然激励着无数人为了理想而编程。
GNU 教会我们:有些事情值得用一生去做,即使这条路充满孤独。
愿我们都能像 GNU 那样,在一个注重效率与消费的时代里,仍旧坚持某些”看起来没那么紧急的理想”。愿我们都有勇气为了心中的信念,选择那条更难走但更有意义的路。
愿我们在数字世界里种下的那些种子——无论是代码、文档,还是思想——都能像 GNU 一样,慢慢发芽,慢慢开花,在时间的长河中绽放出自由的光芒。
愿你我的数字花园,都有机会在岁月中静静开花。
最初写于:2023 年 9 月 27 日
在 GNU 四十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